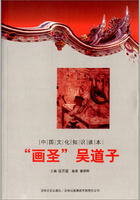硕大的列宁格勒公立图书馆柱廊环抱,内有二十八间阅览室、一千七百万部图书、三十万部手稿、十一万二千张地图,但妮娜·奥金格(Nina Oding)能找到那个存放禁书的特制书柜。20世纪70年代末,奥金格是这家大型图书馆的一名年轻助理,每当无人看管时,她就会七弯八拐地来到特制书柜旁,阅读里面的各种禁书。这些书籍多来自西方,被苏联政府认定具有颠覆性质。类似书籍平时存放在一个上锁的房间,当外国读者提出借阅要求时,它们会被定期放入特制书柜。其他人如果想借阅,总会面临填不完的表格和审批。即便如此,这些书籍通常会莫名失踪导致无法借阅。“抱歉,”馆员会这样解释,“散架了,正在装订。”[1]
这些书籍为什么要秘密存放?政府没有说。这是“发达社会主义”制度莫名的荒唐之一,对不想给人阅读的书籍给予精心呵护。很明显,这些书籍不可能彻底遭禁,因为作为一家创建于1814年的大型图书馆,它不能承认自己没有相应馆藏。于是,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晚期,国家决定把它们一藏了之,差不多吧。
青年学者喜欢把图书馆称作“公墓”(Publichka),在苏维埃思想控制仍然引发焦虑的年代,这里云集了各种自由思潮。内部空间高大的社会学和经济学阅览室被人们称作“社经室”,是几位年轻书目专家的工作地点,他们上懂藏语,下知索尔仁尼琴的全部作品。他们与兴致盎然的读者志趣相投,信任纽带一旦确立,大家便无所不谈。当时,广大读者把图书馆称作“大脑坟场”,并不是因为那里藏有大量书籍,而是因为它云集了头脑聪明的编目专家、图书馆员和众多读者。空气中弥漫着阅读和争论的气息,尤其在吸烟室和咖啡厅,哪怕这里空间狭小,只摆得下几张桌子。[2]
在此聚集的,有克格勃的特工和线人,但禁止踩踏的危险区和红线究竟在哪里,一直没有人说得清楚。国家已经年老多病,充满传奇色彩的触角日渐麻木,大脑开始混沌。然而,不确定性明摆在那里,让谈论的人不敢过于大声。列宁格勒是以其克格勃分支机构异常警觉而著称的。曾有研究人员来到这家图书馆,希望借阅几本禁书。他被告知,馆里没有这样的书。他又来过一次,赫然拿着索书号!他就要借那几本书,因为他知道图书馆有,只是被藏了起来。克格勃展开了调查,索书号从何而来?
对图书馆进进出出的人,妮娜·奥金格是个敏锐的观察者。她身材矮小,长着一头浓密的褐发和一双淘气的眼睛,时而热情迸发,时而严肃忧郁,能一一记住每天来到“社经室”的各色读者。她以脸识人,以借阅证号识人,这些东西她记起来不费吹灰之力。在众多读者中,她记住了一个英俊的高个子年轻人,他满头黄发略带红色,时常在“社经室”流连,阅读着政治经济类书籍。这个人名叫阿纳托利·丘拜斯。
在当时充满好奇心的年轻学者、丘拜斯及其同龄人看来,对于克格勃的害怕还没到草木皆兵的程度,只不过意味着在公共场合说话时确实应该小心而已。这成了人们的第二天性。身边的证据比比皆是,表明时下的制度正在减速,经济和工业生产正在逐渐失灵,领导阶层腐败而自大,但年轻的学者们仍然只能私下嘀咕,互打暗语。他们关于“完善生产方法”的用词,隐晦得犹如位于市中心马拉大街9号的列宁格勒工程经济学院的石质正门。作为一名年轻教授,丘拜斯正在这里崭露头角。
丘拜斯光顾图书馆没多久,奥金格就被分到了他所在的学院。这不是什么挑选。她没把自己当成共产党员,而是一个自由思想者。她认为正由于此,才在大学毕业后被党组织分配到枯燥的应用经济学研究单位。“当时的经济学家就是这些搞笑的人,”她在多年后回忆道,“我觉得自己陷入了某种恐慌。那是一群榆木疙瘩。而且思想古板!而我是一个思想进步的历史学家。”
这样的大学有数百所之多,大批苏联专家在此攻克勃列日涅夫时代未能解决的宏大课题:如何使社会主义更好地发挥作用。小隔间的数量多达上千个,四周摆着相同的黄色木柜,挂着薄布窗帘,桌上放着绿色塑料罩台灯;教室里黑板林立,喝到半干的茶杯横七竖八,苏联的研究人员正在努力寻找“科学”答案,以修复这架生病的社会主义机器。研究人员数年如一日,勤勉地查找着苏联工业体系上那些吱嘎着响的齿轮,只为找到法子,要么推着它转动,要么至少除掉锈蚀。他们寻找着各种“指标”或线索,以确定如何把劳动力提高2%,或者把钢产量提高3%。机器制造、煤炭开采、农业生产、金属冶炼和其他数十个行业,都有自己的研究院所,进行着同样的研究。在苏联社会主义体制下,那个包容一切的、伟大的资本主义市场指标万万没有可能,于是年复一年,数十万研究人员在经济领域里无聊地寻找着非对即错、非好即坏,明显属于虚假的各种措施。很多研究人员心知肚明,或至少有所揣度,他们关于社会主义先进性完美“指标”的探索终将徒劳无益。
分到学院没多久,奥金格就被派往集体农庄,参加一年一度的秋季强制性采收土豆之旅。整个学院倾巢出动,来到列宁格勒州东部边缘地区。这里地处偏远,是苏联帝国的穷乡僻壤,道路泥泞,只有拖拉机能够勉强通行。学院里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研讨班和讨论会接二连三,乡下生活成了深受大家欢迎的休假和放松时间。大家住在陈旧的木制板房里。白天,他们把粗糙的木条箱绑在一起,用来从地里搬运土豆;夜里,他们唱歌、喝酒、聊天。给他们带来生机的,是新鲜的空气、劳累而酸痛的肌肉、阳光暴晒的灼热、新生的友情和邂逅的浪漫。
他们在农场里轮班劳作。奥金格很快就认出了在另一班次参加劳动的丘拜斯。他个子高大,面庞长而英俊,情绪激动或怒火中烧时,立马变得满脸绯红。在大家的印象中,他既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年轻人,也是一个认真负责、毫不做作的领导者。他举止得体,小心谨慎,充满自信。
回到学院后,他做起了“完善社会主义研究与发展”这一课题。据奥金格回忆,丘拜斯既不是正统经济学家,也算不上异己分子。如果总要说点什么的话,那就是他一直非常勤奋,深得老教授们的喜爱。他在很早就被批准入了党,这一点显得颇不寻常。他对暗送秋波的姑娘们不理不睬,始终面带柔和而倔强的笑容,姑娘们一边转身离开,一边大声说着:“真是无可救药!”但跟朋友在一起时,他总能引人注目,语出幽默。一如当时的所有人,丘拜斯喜欢披头士乐队。他喜欢爵士乐,但对“性手枪”(Sex Pistols)和“艾利斯·库珀”(Alice Cooper)这样的乐队从不感冒。他是个非常正直的年轻人。
集体农庄晚上很少有娱乐节目,拖拉机走上好几个小时才能到达最近的电影院。大家于是闲谈至深更半夜。在偏远的乡村,大家摆脱了克格勃的监视。1979年10月的一天傍晚,丘拜斯和来自同一学院的两位朋友就完善社会主义工业这看似永无休止的话题展开了辩论。一位朋友名叫格里戈里·格拉兹科夫(Grigory Glazkov),性格文静,喜欢思考,是工业自动化问题方面的专家。另一位名叫尤里·亚马盖耶夫(Yuri Yarmagaev),是个满含深情的数学家,他能像焊工手里的焊枪一样点子频出。亚马盖耶夫是个反苏激进主义者,格拉兹科夫是个头脑冷静的分析家,对什么想法都要评头论足一番,而丘拜斯属于当权派。丘拜斯二十四岁,两位朋友仅长他一岁。[3]那天晚上的冗长争论,从此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那一年很特殊,”格拉兹科夫后来回忆说,“勃列日涅夫时代具有一定的生命周期性。勃列日涅夫上台的60年代末期,充满了无限的生机。1975年开始进入收尾阶段。那一年是个转折点,社会制度进入解体阶段。到70年代末期,整个制度已经坏掉了。大家对现存的苏联制度完全失去信任,并感到非常失望。任何有脑子的人,都会对这种制度感到非常不满和非常失望。1979年,我觉得这一制度尝试着做了最后一次自我修复。”
这次尝试来自勃列日涅夫下达的一道命令。关于社会主义进步“指标”的无聊探索已经不知所终。经济短缺日渐加剧。工厂为消费者生产出大量劣质商品。于是,各大机构的科学研究人员接到指令,开始了以提高社会主义工业机器质量为目标的重新探索。该项探索工作的蓝图,以勃列日涅夫签署的“第695号令”的形式下发。这是一本厚厚的指示。“它力图成为衡量一切的体系,”格拉兹科夫回忆说,“衡量经济成功与否、工业成功与否、生产力和质量提高与否,等等。这实际上就是尾声。整个制度的各个方面都开始进入尾声。”
就在集体农庄的那个晚上,朋友三人围绕“第695号令”能不能发挥作用开始了争论。
亚马盖耶夫很有把握地认为,该项指令一定会失败。他在工厂里干过。他说,社会主义工业生产完善方案纯属无稽之谈。“全是谎言。根本就没有社会主义经济这回事儿。偷窃和私吞现象比比皆是。”丘拜斯辩称,社会主义经济里有一种为不同群体所秉持的所谓共同“利益”,亚马盖耶夫一下子顶了回去:“我们以工厂厂长为例。他确实有追求。但他的追求,是往自己口袋里多捞钱。”
丘拜斯自信而坚定地支持“第695号令”。他一度立志成为大型工厂的厂长,并亲自研究过社会主义工业衡量标准这一问题。据格拉兹科夫回忆,丘拜斯是个不服输的辩论者。丘拜斯的辩论方法不是就某个论点全盘取舍,而是加以分解,再逐项进行论述。“听着,”据格拉兹科夫回忆,他如此说道,“假定我们这也做了,那也做了,既这样做过,也那样做过,经济为什么还是上不去呢?”
二十多年后,当我向丘拜斯了解当时的辩论经过时,他仍然记忆犹新。[4]“我的确支持‘第695号令’。”他回忆说。当亚马盖耶夫一个劲地抨击这份文件时,丘拜斯觉得自己这位朋友过于感情用事。相比之下,他弄懂了那一大摞文件的实质内容,并真心佩服它的复杂和深度,以及使之成文的专业功夫。他不禁有些恼怒。“他怎么能说整份文件一无是处、漫无目的呢?”想起亚马盖耶夫的长篇指责,他如此说道。
格拉兹科夫转向丘拜斯。他很难把自己想说的东西表达清楚。他知道自己争不过既苛刻又有科学论据的丘拜斯,因为他什么也没有。“我只是凭直觉,这件事情可能性不大。”他回忆说。他告诉丘拜斯,勃列日涅夫的整份文件就像一台结构复杂的永动机。就各个细枝末节,比如飞轮、齿轮、滑轮等,他们几个人可以争论一整夜。然而,格拉兹科夫说,更主要的问题在于,根本没有永动机这回事儿。这就是一场没有结果的探索!起不到任何作用。
格拉兹科夫随后又想到一个更简单的比喻。勃列日涅夫这份文件像一架庞大而复杂的飞机,他如此说道。想想它那结构复杂的机翼、座舱和各个部件的内部连接吧。它全都写在了“第695号令”这份图纸上。但这份漂亮的图纸有一点问题,格拉兹科夫说道。
找不到引擎。
从那天晚上开始,这三位朋友争论不断,一回到列宁格勒,他们就决定要为此做点什么事情。嗓门太大有风险,很可能不会有任何结果。他们决定合写一篇文章,解释关于“指标”的探索为什么以失败收场,即永动机为什么无法正常工作。在丘拜斯的安排下,文章将发表在一份没有名声的刊物上。
他们时常聚会,地点要么在各自家里的厨房,要么在丘拜斯居住的阴暗单间公寓。截稿日期前一天晚上,格拉兹科夫仍然无法把他们的想法写到纸上。“我们一直坐到天亮,天亮时分,他好歹写完了。”丘拜斯回忆说。在他们看来,自己写到纸上的东西是一种革命思想。他们宣称,关于社会主义工业进步虚构“指标”的探索,从本质上说不会有任何作用。旨在衡量工厂产值、劳动和生产过程的各种努力都是白费劲。为什么?这是一个决策人数多达数百万、人为“指标”多达数百项的庞大经济体系,也许没有一项指标能够说得清楚正在发生的经济现象。只有一种强大的工具,能够照顾到复杂的决策全过程,那就是经由自由市场确定的价格。但在当时,也就是1980年,关于价格的讨论很可能招致麻烦。丘拜斯和他的两位朋友一波三折,取得了自以为至关重要的认识,但那又能怎样呢?
*
丘拜斯家里的厨房,时常回响着关于苏联政权、经济、战争和异见等问题的争论。作为两兄弟中的次子,阿纳托利对这些争论的印象十分深刻。他的父亲鲍里斯曾是苏联军队里的坦克手,所在连队于1941年二战爆发时,被围困在立陶宛边境。鲍里斯·丘拜斯奋力突出包围圈,侥幸躲过一劫,后来担任过政委职务,也就是军队里的政治指导员。他对苏联制度的信仰坚不可摧。“我父亲坚信苏联的政权、思想、党威和斯大林,这样的人为数不多。”阿纳托利回忆说。[5]